宋词里的歌声
□ 俞益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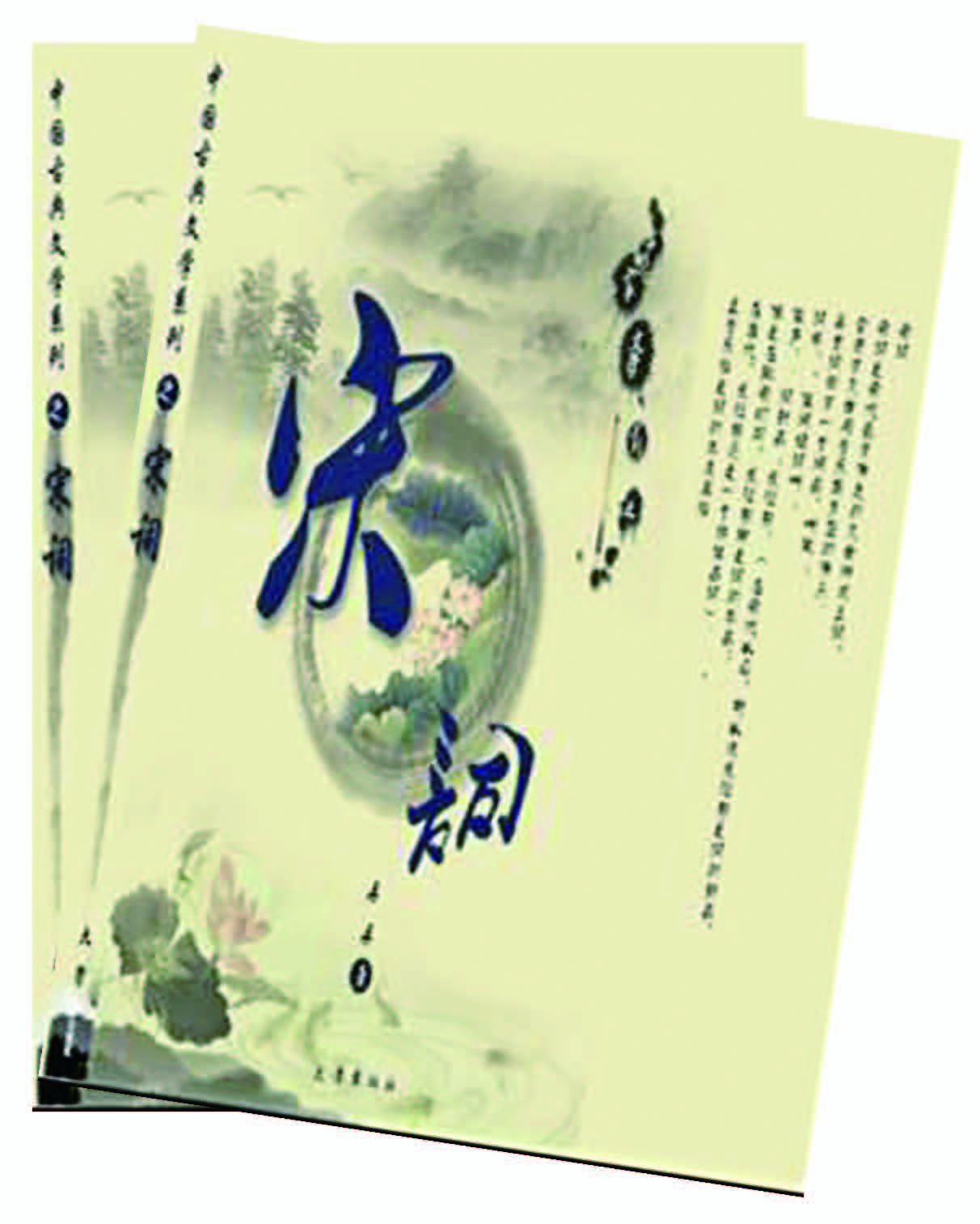
我最喜爱的宋词——包括南唐李煜的《浪淘沙》、《虞美人》、《破阵子》、《相见欢》,这些几乎在儿童时就琅琅上口的词句,当时完全无法体会什么是“四十年来家国”,当时怎么可能读懂“梦里不知身是客”。每到春分,窗外雨水潺潺,从睡梦中惊醒,一晌贪欢,不知道那个遥远的南唐原来这么熟悉。不知道那个“垂泪对宫娥”的赎罪者仿佛正是自己的前世因果。“仓皇辞庙”,离开故国,有那么大的惊惶与伤痛。在一晌贪欢的春雨飞花的南唐,不知道还能不能忘却在人世间久客的哀伤肉身。
每一年春天,在雨声中醒来,还是磨墨吮笔,写着一次又一次的“梦里不知身是客,一晌贪欢”,看渲染开来的水墨,宛若泪痕。我最早在青少年时读着读着的南唐词,竟仿佛是自己留在庙里的一支签,签上诗句,斑剥漫漶,但我仍认得出那垂泪的笔迹。
亡一次国,只是为了让一个时代读懂几句诗吗?何等挥霍,何等惨烈,他输了江山、输了君王、输了家国,然而下一个时代,许多人从他的诗句里学会了谱写新的歌声。
宋词的关键在南唐,在失了江山的这一位李后主身上。南唐的“贪欢”和南唐的“梦里不知身是客”都传承在北宋初期的文人身上。晏殊、晏几道、欧阳修,他们的歌声里都有贪欢耽溺,也惊觉人生如梦,只是暂时的客居,贪欢只是一晌,短短梦醒,醒后犹醉,在镜子里凝视着方才的贪欢,连镜中容颜也这样陌生,“一场愁梦酒醒时”,“无可奈何花落去,似曾相识燕归来”,在岁月里多愁善感,晏几道贪欢更甚,“记得小苹初见”,连酒楼艺妓身上的“两重心字罗衣”都清清楚楚,图案、形状、色彩、绣线的每一针每一线,他都了然于心。
南唐像一次梦魇,烙印在宋词身上。“落花人独立,微雨燕双飞”,唐代写不出的句子,在北宋的歌声里唱了出来。他们走不出边塞,少了异族草原牧马文化激荡。他们多在都市中、在寻常百姓巷弄、在庭院里、在酒楼上,他们看花落去,看燕归来,他们比唐代的诗人少了盛唐气象,更多惆怅感伤,泪眼婆娑,跟岁月对话。他们惦记着“衣上酒痕”,惦记着“诗里字”,都不是大事,无关家国,不成“仙”,也不成“圣”,学佛修行也常常自嘲不彻底,歌声里只是他们在岁月里小小的哀乐记忆。
“白发戴花君莫笑”,我喜欢老年欧阳修的自我调侃,一个人做官还不失性情,没有一点装腔作势。
范仲淹也一样,负责国家沉重的军务国防,可以写《渔家傲》的“将军白发征夫泪”的苍老悲壮,也可以写下《苏幕遮》中“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”这样情深柔软的句子。
也许不只是“写下”,他们生活周边有乐工,有唱歌的女子,她们唱《渔家傲》,也唱《苏幕遮》,她们手持琵琶,她们有时刻意让身边的男子忘了外面家国大事,可以为他们的歌曲写“新词”,新词是一个字一个字填进去的,一个字一个字试着从口中唱出,不断修正,“词”的主人不完全是文人,是文人和乐工和歌妓共同的创作吧!
了解“宋词”产生的环境,或许会觉得:我们面前少了一个歌手。这歌手或是青春少女,手持红牙檀板缓缓倾吐柳永的“今宵酒醒何处”,或是关西大汉执铁板铿锵豪歌苏轼的“大江东去”,这当然是两种不同的美学情境,使我感觉宋词有时像邓丽君,有时像江蕙。同样一首歌,有时像酒馆爵士,有时像黑人灵歌。同样的旋律,不同歌手唱,会有不同诠释。鲍勃·狄伦(Bob Dylan,1941-)的《Blowin' in the Wind》,许多歌手都唱过,诠释方式也都不同。
面前没有了歌手,只是文字阅读,总觉得宋词感觉起来少了什么。
柳永词是特别有歌唱性的,他一生多与伶工歌妓生活在一起,《鹤冲天》里“忍把浮名,换了浅斟低唱”,“浅斟低唱”是柳词的核心。他著名的《雨霖铃》没有“唱”的感觉,很难进入情境。例如一个长句——“念去去千里烟波,暮霭沉沉楚天阔”,停在“去去”两个声音感觉一下,我相信不同的歌手会在这两个音上表达自己独特的唱法。“去去”二字夹在这里,并不合文法逻辑,但如果是“声音”,“去”、“去”两个仄声中就有千般缠绵、千般无奈、千般不舍、千般催促。这两个音节挑战着歌手,歌手的唇齿肺腑都要有了颤动共鸣,“去”、“去”二字就在声音里活了起来。可惜,宋词没有了歌手。
找不回来,命中注定该湮灭的也就湮灭了。片言只字留存在图书馆,让后世学者寻章摘句,想象或拼凑最初的面貌。那已经不干我事。
本期推荐
NEWS RECOMMENDED
《溧阳日报》溧阳市融媒体中心版权所有◎All Rights Reserved
江苏路特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仅提供技术服务支持
文字、图片、视频版权归属发布媒体










